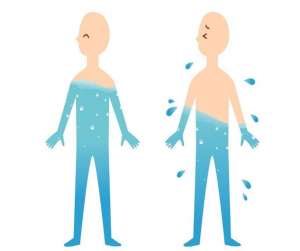养猫以后不来月经养猫的故事
...送走我妈的那天,我乘地铁返回。出了青年路地铁,天已放晴,骑上自行车往姚家园走。路过那个红绿灯口,看到卖猫的阿姨还在,挪威森林猫在笼子里转来转去,毛发鲜亮,精神十足。我锁了车,向她走去,她微笑着跟我打招呼,问我怎么没跟阿月一起,是否已决定要买。我没回答,把她拉到一个角落。
我手里夹着烟,靠在墙上,跟她秘密谈论着什么。她一开始极不情愿,直到我转给她两千块钱,她笑着说,想让猫得上什么病,都有操作的办法。我蹲在墙角,连续抽了几根烟,起身时脑袋一阵眩晕,险些摔倒。骑上车,继续往姚家园走……
终于,坑被完全填平,猫不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折断一根树枝,把几片叶子洒在上面,看上去毫无痕迹。回去的路上,雷声滚滚,但雨已经不下了,西边的天空出现一道锋利的霞光,未见太阳。猫砂盆、猫粮、猫砂全都在放在门外,三层高的猫窝被拆成一块块木板,散乱地堆积在一起。是她扔的,有那么一刻,我甚至想把它们搬出去,再次掩埋。
我走进卫生间,匆匆洗了个澡。我钻进被窝,紧紧地搂着她,直到一跃而上。运动地越快,她搂地越紧,彷佛要把手指扣进肉里。紧要关头来临,我强行抓住她的双臂,摁在床上,避免她再次把我推开。然而,这次她却毫无挣扎,似乎早有准备。我瘫软在她身上,剧烈喘气,一阵抽搐,一阵满足。
最后,我想到母亲,脸上露出微笑。
1986年到1991年,五年间,母亲共生了五个孩子。前两胎都是女孩,正是后来我的两位姐姐。第三胎和第四胎是男孩,一个刚出生就夭折,另一个活了二十多天,在镇医院停止了呼吸。在我们那,婴儿不准入祖坟,不准立碑,甚至连单独起坟都不允许。两个婴儿都是母亲埋葬的,除了她,没人知道他们埋在哪里。家里人说法不一,有的说扔进了河里,有的说,埋在了隔壁村,有的说,就埋在我们自家地里的某个位置。
失去两个男婴的母亲,更加迫切地想要个男孩。1991年,我出生,但因为计划生育,母亲被拉去结扎,二姐不得不被送到姥爷家,和姥爷一个姓。直到姥爷去世,母亲才把她接回来,当时她已经十二岁,从此没喊过一声爸妈。十六岁那年,她随爸妈去上海打工,在电子厂里认识一个广东人,一年后,两人消失的无影无踪,之后再也没跟我们联系过。
正如当初失去那两个男婴一样,失去二姐后,母亲变得更加迫切地想要孩子,随着时间的推移,愈演愈烈,希望寄托到了下一代。大姐后来嫁到了浙江,有个女儿,但她们常年不回娘家,五年来只见过一次。我成了她最大的希望,这希望自然不再是我本人,而是我的孩子。
第二个月,阿月没来例假,去医院检查,果然怀了孕。我把消息告诉母亲,她喜极而泣,在电话里几乎哭出了声。然而,当我以为真的实现了母亲的愿望时,没过多久,事情又有了新的转变。
那天傍晚,她下班回来,走路蹑手蹑脚,像是扭到了腰,我上去搀扶,她冲我邪魅一笑。放下包,她走进厨房,拿起铁丝网,挤上一些洗洁精,开始清洗台面和灶具。接下来,说话的同时,她手也没停过,身体始终微微前倾。
她说,记得吗,有一次你喝醉了,在车里嚎啕大哭。我说,记得,你知道的,我这人一喝大就哭,后来就断片了。她说,断片了,但你仍可以说话。我说,我说了什么?她说,那时候黑塞还在,还好好的。我说,是的,真可惜了。她说,你说你妈告诉你,女人失去一个东西,就会通过另外一个东西获得补偿。我顿时心跳加速,面部赤热,无法回话。
她继续说,黑塞原本是好好的,你知道我喜欢它,于是怂恿我把它买回家,而在这之前,你就先让那阿姨把它感染上猫瘟。我靠在墙上,看到她嘴角洋溢着一丝可怕的微笑。她说,其实,何必那么大费周折,以为我失去一只猫,就会想生孩子补偿,这是你妈的逻辑?还是你的逻辑?
我没回答,眼睛死死地盯着地板上的花纹。她说,不管是谁的逻辑,我陪着演了下去,假装带黑塞看病,假装跟医生较真,假装骂那阿姨一顿,不过,为黑塞流的眼泪倒是真的,想换家医院救它只是一时冲动,清醒之后我明白,你不可能让我把它救活,即使救活了,你总有其他方法置它于死地。
我抬头望望她,铁丝网摩擦灶台,发出滋滋声。她说,最后,还故意成全你,怀了孕,你证明了自己很行,但不是向我爸证明,而是向你妈证明。我身体沿着墙缓缓滑下去,蹲在地上,仍未说话,似乎已预感到结局。她说,你妈这辈子也是够惨的,失去两个儿子,才生出你,代价是牺牲你二姐,凭什么?你二姐有什么错?
我说,是的,二姐没错,是我妈的错,但她不能再失去了。她说,所以我就得陪你一起承担?就得牺牲黑塞?就得生孩子满足她?在你喝醉的那天夜里,我就做好了失去黑塞的准备,同时,一个不顾后果的计划也正涌向我,我知道这么做对我没有任何好处,但对她同样如此。
那冷笑声里夹杂着铁丝网的滋滋声,像条毛虫钻进我的耳朵,又顺着难以琢磨的路径直达脑袋。她把铁丝网扔进洗菜池里,转向我,从兜里掏出一张单子,向我扔来。浅黄色的纸张在空中飘飘荡荡,粘着几滴水珠,随着水滴在纸上蔓延开来,那两个令人的绝望的字逐渐清晰,悬在我的头顶,仿佛千斤重鼎一样压向我。
一切都结束了,我蹲在地上,腿部发麻,良久站不起来。
深夜,我站在窗口抽烟,暗夜里接连传来狗吠声,悠远寂静,中国尊大楼规律地闪着灯光,城市的欲望也在睡眠,待到黎明来临,向人们发起新一轮攻势。我望了望卧室,装满衣物的三个纸箱靠墙排放,粉色行李箱立在门后。她躺在床上,闭着眼睛,面部庄严肃穆,被子随着呼吸起起伏伏。
我期待第二天会有新的转变,什么事都没发生,屋里所有东西都不会消失。这种想法逐渐膨胀。我把烟头弹进夜色中,火星划出一道弧线,最终遁入无边的黑夜。那呼吸声越来越大,在这个寂静之夜,成为唯一能够捕捉到的具有生命迹象的声音。我抬起轻飘飘的双腿,走到床边,盯着盖在她身上起起伏伏的被子,呼出的空气几乎打在了我脸上,一种灼烧感扑面而来。
另一个枕头在她头边,中间凹陷出半个脑袋大小的坑,她总说我脑袋太大,容易把枕头压变形,准备为我换个软点的,还没来得及。今夜它的主人将最后一次使用它,但不再是把它枕在头下。我越过她的身体,拿起它,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影影绰绰。风透过纱窗吹进来,阳台上挂着的衣架发出咯吱咯吱声,衣服的影子在墙壁上时隐时现。坑开始缓缓下移,那呼吸已无法打在我脸上了,被子也将不再起伏。
完